作者:张艾
一、引言 贾宝玉是《红楼梦》中第一主人公,荣国府嫡派子孙,贾母的掌上明珠。他出身地位不凡,又聪明灵秀,是贾家寄予重望的继承人。不过书中还有另一个宝玉,就是金陵甄府“甄应嘉”之子——“甄宝玉”,从开篇到结尾,甄宝玉时不时出现,他似为贾宝玉的镜中幻影,与之呼应。书中安排这“真”“假”宝玉到底有何玄机呢?正如太虚境中的一幅对联中写道“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也无。”这甄、贾宝玉到底孰“真”孰“假”,通过几处对比就可见分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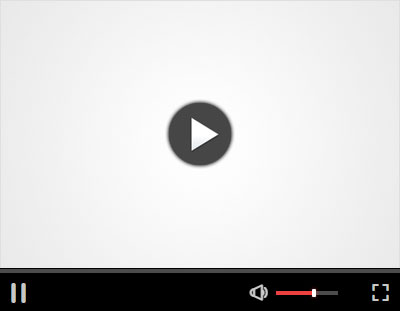
二、四处对比可知宝玉“真”与“假” (一) “神”与“凡”的对比 贾宝玉出场前就与神话色彩紧密相连——女娲补天遗留下的一块未用的石头。顽石有些灵性,化为人形,被警幻仙子留在赤霞宫中,做了“神瑛侍者”,对“绛珠仙草”有灌溉之恩。顽石又被一僧一道点化成一块美玉,镌上数字,正面是:“莫失莫忘、仙寿恒昌”,反面是:“一除邪祟、二疗冤疾、三知祸福”,并命名为“通灵宝玉”。一种说法是:贾宝玉由神瑛侍者脱胎而成,衔玉而生;另一种说法是:“通灵宝玉”、“神瑛侍者”和“贾宝玉”三者合为一体。 书中第二回“冷子兴演说荣国府”就介绍了人尽皆知的一奇事,荣国府的子孙——贾宝玉“一落胎胞,嘴里便衔下一块五彩晶莹的玉来,上面还有许多字迹,万人皆以为奇,说他来历不小。”这一吉兆自然就给贾宝玉的身世蒙上一层朦胧的神话色彩,显然他是书中有意安排的具有特殊灵性的人物,而甄府中的宝玉出场前后都没有任何的神话色彩。书中人物除黛玉外,也没有与开篇的神话有任何关联。从这一点来看,更加对比出,谁是神仙下凡,谁是凡夫俗子。 紧接着又借贾雨村之口介绍了“甄宝玉”是“其暴虐浮躁,顽劣憨痴,种种异常。”他还常对小厮们说“这女儿两个字,极尊贵,极清净的……凡要说时,必须先用清水香茶漱了口才可,设若失错,便要凿牙穿腮等事。” 根据镜像人物“相似相反”的原则,这甄、贾宝玉的表面性情貌似相同,内心世界却是截然相反的,贾宝玉心地善良、待人真诚,有超越阶级的平等博爱之心,何曾会做“凿牙穿腮”之事?而甄宝玉“暴虐浮躁,顽劣憨痴”,内心世界是非常残忍的。由此更加可知,甄宝玉本身只是个“凡胎浊物”,而贾宝玉才是“神瑛”下凡。 (二) “奇”与“俗”的对比 贾宝玉相貌出众“面如敷粉,唇若施脂,转盼多情,语言常笑。天然一段风骚,全在眉梢;平生万种情思,悉堆眼角。”他自幼天资聪慧,虽不屑于读「圣贤书」,却有着过人的才华与灵性。从大观园贾政试才情可看出,他文才超凡脱俗,第七十八回为晴雯所写的《芙蓉女儿诔》更是一绝。在警幻仙姑的眼中他“天分高明,性情颖慧。”冷子兴说他“虽然淘气异常,但其聪明乖觉处,百个不及他一个。”以及“宝玉平日胡乱写的诗词传出之后,被市井的读书子弟所喜欢,甚至有向他来求诗词的。”这些都可以看出贾宝玉是天分极高的“奇”人。 在后续书中第一百二十回也写了,这个平时对于圣贤书大半夹生,断不能背之人,被逼参加科考居然高中第七名举人,而一向苦读的贾兰却只考了第一百三十名,连一向不看好他的父亲最终也不得不承认他的灵性是凡人所不能比的。 父亲贾政道:“你们那里知道,大凡天上星宿,山中老僧,洞里的精灵,他自有一种性情。你看宝玉何尝肯念书,他若略一经心,无有不能的。他那一种脾气也是各别另样。” 这都说明贾宝玉的才情与灵性是凡人所不能比的“奇”人。 甄宝玉年龄比贾宝玉小一岁,虽与贾宝玉有着相同的外貌,但却没有玉。贾宝玉的“玉”是日夜不离、如影随形,丢了“玉”便失去心智。它像是宝玉的护身符,更像是宝玉的灵魂。最重要的是“玉”是宝黛爱情的见证者,红楼梦中所写的故事都是由这块石头记载着。可见,这“玉”在书中的地位非同一般,而甄宝玉为何却没有“玉”? “玉”是集天地之精华而成,具有灵性,超凡脱俗的宝物,自古以来就是高贵、纯洁的象征。因此,是否有“玉”对于“真”“假”宝玉也是非常重要的。众所周知,曹公对书中人物的起名是颇有寓意的,名字中带“玉”的四人:贾宝玉、林黛玉、妙玉、林红玉,都是书中所歌颂的正面人物,性格中都带有玉的特质——超凡脱俗、一身傲骨、追求真我、不入世俗。唯独这“甄”宝玉改变原有的真性情,最终落入经济仕途的官场,成为一俗人。
甄宝玉的性情开始也跟贾宝玉有相似之处,不愿走仕途,不愿读书,他说:“必得两个女儿伴着我读书,我方能认得字,心里也明白,不然我自己心里糊涂。……因此,他令尊也曾下死笞楚过几次,无奈竟不能改。” 甄家先于贾家获罪被抄,在后四十回续写甄宝玉为重振家业,参加科考中举,并娶李绮为妻;而贾宝玉在贾家被抄后,虽科考高中第七名,但终不愿落入尘网,遁入空门,跟着一僧一道做了和尚。石头又回到青峰之下,所记载之事被一空空道人从头至尾抄录回来,成为问世传奇。——“无才可去补苍天,枉入红尘若许年。此系身前身后事,倩谁记去作奇传?” 从开篇到结局,通过上述“奇”与“俗”的对比就更加显而易见,这甄、贾宝玉镜像中的二位人物,到底孰“真”孰“假”了。 (三) “正”与“邪”的对比 书中开篇第二回,借贾雨村之口将天地生人分为大仁大恶两种,并将甄、贾宝玉评为正邪两种人格的典型:贾宝玉评为“正”——“置之于万万人中,其聪俊灵秀之气,则在万万人之上。”;而甄宝玉却为“邪”——“这等子弟,必不能守祖父之根基,从师长之规谏的。”那么反观二人的性格特征与人生抉择,这个评价是否是作者的本意呢?通过几处对比便可知。 首先,甄、贾宝玉的“女儿论”具有本质上的差异。 贾宝玉在七八岁时就发表了惊世骇俗的“女清男浊”论:“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 表面上看是对女儿的赞美之情,实际上却蕴含着生命的真谛。在当时的男权社会,男人们占据了统治地位,女子处于被压迫的地位,只能依附男人生存,而男人的世界就是一潭污水。书中从宁、荣二府,到贾、王、史、薛四大家族,对男人们的荒淫、丑恶、无情、凶残描写的淋漓尽致,而“神瑛”下凡的贾宝玉所追求向往的是真、善、美,这些人性中美好的一面只能在深居闺阁之中的女儿们身上看到,她们心地善良、美丽聪慧、多才多艺,她们大多数的命运是悲惨结局,令人倍感心痛。他深刻感悟到:“天生万物之灵,凡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钟于女儿,须眉男子不过是些渣滓浊沫而已。”与她们相比,自己也是个浊物了,因此他不愿进入男人的世界,逃避长大、逃避家庭责任,只愿在留在闺阁之中。由此可见,贾宝玉的女儿情是直觉的、纯真的,建立在人权平等的基础之上的。 而甄宝玉的女儿论原文是这样描述的,他说:“必得两个女儿伴着我读书,我方能认得字,心里也明白,不然我自己心里糊涂。”又常对跟他的小厮们说:“这女儿两个字,极尊贵,极清净的,比那阿弥陀佛,元始天尊的这两个宝号还更尊荣无对的呢!你们这浊口臭舌,万不可唐突了这两个字,要紧!但凡要说时,必须先用清水香茶漱了口才可,设若失错,便要凿牙穿腮等事。”
甄、贾宝玉的女儿论好似同出一辙,仔细品读就觉得大相径庭了。甄宝玉把“女儿”二字提升到极其尊贵的地位上,浊口臭舌的小厮们不能随便说,说错了就要凿牙穿腮,而自己不但可以说,还必得要两个女儿伴着才能读书识字。表面上看是对女儿的尊重,实质上是把人分成等级,女儿的地位远远高于小厮,自己的地位却是最尊贵的,女儿要常伴着我,为己所用的。可见,甄宝玉内心世界是既自私又残酷的。这与“怡红公子”的平等博爱刚好相反,“怡”就是快乐,“红”在传统文化中代表女性。用他的话来说,是为女儿们操碎了心,他是为女儿们而存在的,只有付出并无索取的自私想法。 其次,甄、贾宝玉对仕途人生道路的选择也不同。 书中多次描写贾宝玉厌恶世俗,玩世不恭。他鄙视官场上阿谀奉承的伪君子,讽刺那些求取功名的人是“国贼禄鬼”。曾因湘云劝他学些仕途经济的学问而恼羞成怒,与宝钗的隔阂也源于对仕途的看法不同,二人的婚姻最终因三观不合而导致分道扬镳。在后四十回的续写中,甄宝玉走仕途道路,留在尘世,重振家业。虽然这未必是曹公的亲笔,但基本延续了他本人的意愿。作为贾宝玉的镜像人物,甄宝玉一定会做出不一样的人生选择,贾宝玉步入空门,而甄宝玉势必会走入仕途。甄、贾宝玉究竟孰“正”孰“邪”呢?甄宝玉功成名就、重振家业不就是贾府上下对贾宝玉的殷切期望,不就是正路吗?我想不同的人会给出不同的答案吧。 在世人的眼中,考取功名就是人生的最高追求,重振家业就是贾家子孙的责任所在。但作为“神瑛侍者”和“绛珠仙草”下凡贾宝玉和林黛玉就不这么认为,所以贾宝玉说:“林妹妹不说这样混账话,若说这话,我也和她生分了。”而甄、贾宝玉在后续中唯一一次见面谈心,贾宝玉却是这样评价甄宝玉的“只是言谈间看起来并不知道什么,不过也是个禄蠹。他说了半天,并没个明心见性之谈,不过说些什么文章经济,又说什么为忠为孝,这样人可不是个禄蠹么!只可惜他也生了这样一个相貌。我想来,有了他,我竟要连我这个相貌都不要了。他现在才知道这个宝玉不是他少年梦中梦到的宝玉,不是他少年听别人说起的宝玉。薛宝钗却说人家这话是正理,做了一个男人原该要立身扬名的。”由此可知,贾宝玉与林黛玉是心灵相通的,甄宝玉与薛宝钗才是同路人。或许在甄宝玉、薛宝钗等世人的眼中贾宝玉是无用的“富贵闲人”。而在“绛珠仙草”眼中,她的“神瑛侍者”是无人可替代的。 再从书中所描写贾雨村的仕途之路,可知官场确实是藏污纳垢,让人迷失良知的地方。贾雨村从起初不懂官场规矩而被罢免,到“葫芦僧判葫芦案”,直至为讨好贾赦居然设计诬陷石呆子,欺压良民,已经蜕变成一个利欲熏心的官吏,如本从良知是很难在官场上立足的。对于一个“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的“神瑛侍者”必定是所不能容忍的。而贾宝玉无疑是作者所大力肯定的人物,从他的灵性、他的才华、他的平等博爱以及他对人性中真善美的追求就可知,曹公是借贾宝玉这一人物,来对世人表白自己人生观与价值观。 最后,还要说明贾宝玉对权势名利的追求态度有别于他人。 贾宝玉唾弃功名权势,是不是说名利本不可求呢?这个观点从宝玉见北静王与贾雨村时的态度对比就可以看出。 第十四回贾宝玉路谒北静王写道: “那宝玉素日就曾听得父兄亲友人等说闲话时,赞水溶是个贤王,且生得才貌双全,风流潇洒,每不以官俗国体所缚。每思相会,只是父亲拘束严密,无由得会,今见反来叫他,自是欢喜。一面走,一面早瞥见那水溶坐在轿内,好个仪表人材。” 第三十二回写道: 有人来回说:“兴隆街的大爷来了,老爷叫二爷出去会。”宝玉听了,便知是贾雨村来了,心中好不自在。袭人忙去拿衣服。宝玉一面蹬着靴子,一面抱怨道:“有老爷和他坐着就罢了,回回定要见我。”史湘云一边摇着扇子,笑道:“自然你能会宾接客,老爷才叫你出去呢。”宝玉道:“那里是老爷,都是他自己要请我去见的。”湘云笑道:“主雅客来勤,自然你有些警他的好处,他才只要会你。”宝玉道:“罢,罢,我也不敢称雅,俗中又俗的一个俗人,并不愿同这些人往来。” 北静王与贾雨村同是官场中人,贾宝玉对二人的态度却截然不同。如果是“不以官俗国体所缚”的贤王,贾宝玉是愿意结交的;如果是那些唯名是图而失去自我的人,贾宝玉就不屑于与之来往。可见,官商权贵未必都是浊物,浊的是为名利权势所累的人。贾宝玉更看重的是人品及做人生态度。 (四) 曹公与贾宝玉的对比 曹公晚年的生活非常窘迫,以卖画为生。住的地方是“山村不见人,夕阳寒欲落。”过的日子是“满径蓬蒿老不华,举家食粥酒常赊。”在生活窘迫的状态下,却依然坚持自己的梦想“批阅十载,增删五次”,著成这传世伟大之作,可谓“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为了写《红楼梦》不知付出多少血泪,可以说他一生都在写《红楼梦》。人的一生有几个十年,以曹公的才华,用十年的时间去考取功名或者混口饭吃未必不能,为何他花十年的心血去写一本世人作为茶余饭后的闲书呢?这个“痴”与书中贾宝玉极其相似。贾宝玉的痴狂就是曹雪芹自己的本性,能读懂贾宝玉之人就是读懂曹公之人。正可谓“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其实每个人的内在都一个真假宝玉,到底哪个才是真宝玉?当我们习惯把假的当成真的,就真正的迷失了自我。“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也无。”只有分清何为真、何为假、何为有、何为无,才不会为假像所惑而迷失真我。在当今社会物欲横流的金钱社会,有谁还能像曹公一样坚持真理、保持真我本性,有谁能不随波逐流,不入世俗?当你脱去虚伪的外壳真实地面对你自己时,你是否可以坦然的面对那个真实的你! |